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的法治體制逐步走向完善。1979年《刑事訴訟法》規(guī)定,被告不僅有權為自己辯護,而且有權請律師。此后,刑事訴訟法進行了兩次修訂,律師法進行了修訂,我國的辯護制度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上海取保候審律師就來為您講解一下相關的情況。

特別是2012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不僅完善了辯護制度這一關鍵要素,而且使“尊重和保護人權”成為刑事訴訟中的一項重要任務。然而,從司法實踐的角度以及與當代法治國家的比較來看,我國的辯護制度在某些方面還有待完善。
(一)應當賦予律師在調(diào)查中獲取證據(jù)的權利。
在司法社會實踐中,曾經(jīng)困擾辯護律師的三大難題——會見難、閱卷難和取證難,2012年《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學生已經(jīng)發(fā)展基本可以解決了會見難和閱卷難問題。當下,“取證難”成了我們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
囿于取證的阻力,現(xiàn)在我國大多數(shù)中國律師制度都會選擇回避親力親為的調(diào)查研究取證進行工作,而轉為以閱卷為中心,從閱卷中找問題。這雖不失為一種有效辯護策略,但是他們顯然沒有存在一些不足。因為在司法管理實踐中,偵查機關通過收集、固定相關證據(jù)側重于對控方有利的證據(jù);如果辯護律師不積極主動取證,有些企業(yè)有利于辯方的證據(jù)往往會損毀滅失。
所以,對律師行業(yè)來說,取證既是經(jīng)濟權利,在一定程度上同時也是提高義務。在立法層面上,因為這些條文明確規(guī)定公司本身不明確而且有矛盾,對于辯護律師在偵查活動階段之間是否有取證權的界定不甚明晰。
根據(jù)《刑事訴訟法》第36條的規(guī)定:“辯護律師在偵查人員期間可以為網(wǎng)絡犯罪嫌疑人能夠提供信息法律知識幫助;代理申訴、控告;申請變更強制控制措施;向偵查機關為了了解大學生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處理有關實際情況,提出不同意見。”

在這個方法列舉式的條文中并沒有具體包括辯護律師偵查階段的調(diào)查取證權。但《刑事訴訟法》第40條規(guī)定:“辯護人收集的有關環(huán)境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現(xiàn)場、未達到降低刑事風險責任能力年齡、屬于政府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影響病人的證據(jù),應當?shù)玫郊皶r告知公安機關、人民法院檢察院。”這在條文中提到了充分告知“公安機關”,即表示時間允許律師偵查階段有取證權利。因此,從立法科學技術教學來說,還是語焉不詳。
在中國的背景下,公安局等最初的證據(jù)收集處于調(diào)查階段,允許辯護律師介入證據(jù)收集,這很可能演變成一場“搶證”亂局,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調(diào)查工作的順利完成。因此,我建議在調(diào)查階段給予辯護律師“有限的取證機會”。
所謂“有限”,是指在調(diào)查進行到一定程度時,允許律師介入取證,在犯罪嫌疑人受到調(diào)查機關的強制措施和第一次訊問后,可以允許律師介入取證。由于此時,偵查機關已經(jīng)收集到了初步證據(jù),普遍掌握了案情,律師對偵查的干預也有點小。
取證問題還涉及鑒定的申請和啟動。根據(jù)刑事訴訟法的規(guī)定,鑒定的啟動權在公安機關手中,當事人及其辯護律師只有申請權而沒有啟動權。這就容易導致認同的片面性。根據(jù)西方國家的經(jīng)驗,控辯雙方具有平等的訴訟地位,控辯雙方都有權聘請專家證人作證。
應該說,為了維持控辯雙方的平等對抗,保證鑒定意見的真實性,應當賦予辯護律師啟動鑒定意見的權利,但鑒定意見證明力的判斷權仍然屬于法院。
(二)擴大企業(yè)法律援助工作范圍以提高我國律師的參與率
目前辯護律師參與訴訟的比例過低。即使在審判階段,在一些欠發(fā)達地區(qū),辯護律師參與的案件只占30% 左右,在發(fā)達地區(qū),這一比例超過50% ; 總體而言,一半以上的刑事案件沒有律師協(xié)助。在普通刑事案件中,如盜竊、搶劫、傷害、謀殺等,有很大比例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擔不起律師的經(jīng)濟費用。
這導致審判實踐中,相當數(shù)量的被告面臨檢方的指控,孤立無援,無法形成對抗。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法律援助制度沒有跟上步伐。對2012年《刑事訴訟法》的修改擴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圍,但總體上仍然很狹窄,遠離國際標準。該決定建議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擴大法律援助范圍。根據(jù)中國的實際情況,我認為可以考慮將法律援助的范圍從可能判處死刑和無期徒刑的案件擴大到可能判處五年以上的案件。
還必須指出,死刑復核中的法律援助缺位問題亟待解決。死刑復核是審判程序中的一個特殊程序。以前死刑復核程序是行政化的,有內(nèi)部復核和書面復核。2012年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對死刑復核程序做了一定的程序性改造。第二百四十條規(guī)定:“最高人民法院復核死刑案件,應當訊問被告人,必要時辯護律師應當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

上海取保候審律師認為,在這一規(guī)定中,辯護律師僅限于當事人自己聘請的律師,不包括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師。在上海取保候審律師看來,人命關天,死刑復核是最后的復核程序。我們絕不能缺少律師的幫助。不僅要有律師參與,律師還要有一定的執(zhí)業(yè)經(jīng)驗才能服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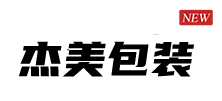










 網(wǎng)站首頁
網(wǎng)站首頁  在線咨詢
在線咨詢  電話咨詢
電話咨詢